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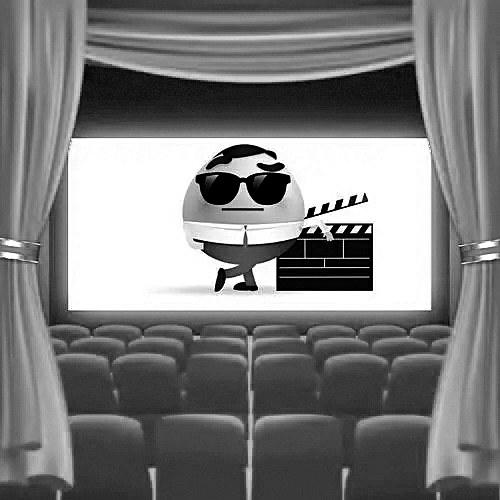
資料圖片
2023年電影暑期檔正在火熱進行,近80部中外影片開啟了一場大戰。與此同時,屏攝“打卡”再度成為社會公眾爭議的話題。
對于觀眾在觀影期間利用手機等電子設備對銀幕進行攝影、錄像并將拍攝內容上傳至網絡空間的行為,電影行業表示強烈抵制。屏攝行為的法律紅線在何處?在社交平臺上發布屏攝內容是分享自由還是版權侵權?具有營利目的是屏攝行為構成版權侵權的必要條件嗎?這些問題都值得大眾警惕和深思。
屏攝行為并非都違法
觀影“打卡”是分享愉悅生活的一種方式,然而法律之下的自由方才是真正的自由。屏攝行為不僅是對觀影禮儀的悖論,還可能觸及法律紅線。以票根收藏替代銀幕攝影,以海報宣傳替代視頻錄像。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拒絕屏攝,要從每一個人做起。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未經許可,對正在放映的電影進行錄像是屬于違法行為。《電影產業促進法》第31條明確禁止對正在放映的電影進行錄音錄像。所謂“錄像”,是指攝制任何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連續相關形象、圖像,拍攝視頻是典型的錄像形式。近年流行于各大社交平臺的實況圖片,又稱“live圖片”,其本質亦是無伴音的連續圖像集,故而實況拍攝是受上述條文規制的錄像行為。在電影放映期間,擅自對銀幕進行視頻錄制或者拍攝實況圖片,構成對《電影產業促進法》的違反,電影院工作人員有權進行制止,并要求其刪除屏攝內容,更甚者,可要求其離場。
以個人欣賞、評論說明為目的,少量拍攝電影靜態照片可以構成合理使用。電影是基于視覺暫留原理形成的“圖片集”,單幀畫面是構成電影的基本表達,屬于電影作品的一部分,可以受到《著作權法》保護。靜態攝影是對單幀畫面的復制,落入復制權控制的范疇。如果“隨手拍”是出于留作紀念、與特定朋友分享等個人欣賞、評論說明的目的,未影響電影作品的正常使用,也未不合理地損害電影制作者的合法權益,則屬于為《著作權法》所容許的合理使用行為,可以不經過電影制作者許可,也無需支付報酬。但即便如此,屏攝行為仍可能降低其他觀眾的觀影體驗,有悖于文明觀影禮儀,不值得提倡。
公開傳播屏攝內容侵犯版權
使不特定多數人能夠感知電影畫面即為公開傳播行為。電影行業極力反對屏攝行為是源于對屏攝內容遭到公開傳播而影響票房實績的擔憂。《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公開傳播”強調在不轉移作品有形載體的前提下,使正常社交范圍之外的不特定多數人得以感知、欣賞作品。由于受眾之間緊密度較低,通常情況下,未設置可見分組的朋友圈、微博等屬于半公開或者公開場合,在此類社交平臺上發布屏攝內容構成公開傳播。值得注意的是,上傳屏攝照片、視頻,使其處于不特定公眾想感知就能夠感知的狀態,即構成公開傳播,相關動態的瀏覽量高低并不影響公開傳播行為的成立。
在社交平臺上公開發布屏攝內容構成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以配圖、小視頻等形式將屏攝內容分享至開放的網絡空間進行觀影“打卡”是時下流行的一種社交文化。與此同時,該行為使公眾可以在其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登錄社交平臺,在線欣賞或者點擊下載相關電影作品的片段,構成交互式傳播,應當受到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規制。將屏攝內容上傳至網絡空間涉及對作品的復制,但由于此處復制作為實現交互式傳播的手段,其所造成的損害最終呈現為非法交互式傳播造成的損害。因此,侵犯復制權的法律責任在此情境中不再單獨認定。
營利目的影響屏攝行為定性
具有營利目的不是使版權侵權成立的必要條件。根據行為是否直接落入專有權利控制的范圍,侵犯版權可以分為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就直接侵權行為而言,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過錯并不影響侵權行為成立,它僅僅影響責任承擔方式和損害賠償數額。具有營利目的是對行為人實施侵權行為時心理狀態的描述,說明其積極追求侵權損害后果,存在主觀故意。在未經權利人許可且無法定免責理由的情況下,擅自拍攝并公開傳播電影畫面、片段,即構成對視聽作品復制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直接侵權,以營利為目的且情節嚴重的,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
以營利為目的進行拍攝與傳播存在構罪風險。根據我國《刑法》第217條,侵犯著作權罪以營利目的為構成要件。具有營利為目的表明行為人以拍攝和公開傳播屏攝內容為手段而謀取非法利益,主觀惡意明顯。對于巨額利潤的追求往往導致行為人選擇多次重復實施侵權行為,不斷擴大犯罪規模,這將嚴重破壞市場競爭秩序。以營利為目的,未經權利人許可,復制發行、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電影作品,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 元 以上、非法傳播作品數量合計在500部以上、實際被點擊數達5萬次以上或者注冊會員達1000人以上的,構成侵犯著作權罪。